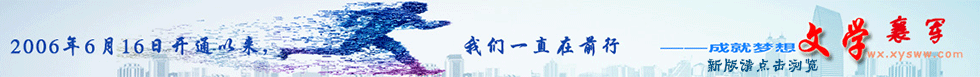������˹��ת�������뿪�����Ѿ�30���ˣ�ÿ������ڵ������ֵܶ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ϣ���Ĺ���űޡ���ֽ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ܿ��Ŀ��֣����ٺ�����
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dz����Ϻӿڳ����С�ʼ�ͥ����ĸ�����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˳����Ľ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磨�����ѫ�������ŵĸ������ֵ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Ϊ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̻����ŵĸ��Ͷ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ţ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̡����ŵ���Ҿ����Ϲ⻯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Ժ�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˿���ĸ���ҽԺֻ��һǽ֮�������ӹ�¥Ҳֻ������Ժ�ӡ�ĸ��1928��4��27�վ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ĸ���ҽԺ���ĸ�׳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Ĭ��Ĭ�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۾���ҽ�����й������պ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ի�����˼ң����϶�˾³��կ�����Ϻӿ�����ֺ��ҵ��ӿ�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ɳƹ����У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ֵ��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ĵ���Ҳ�ں��ҵ��ӣ���³�ҵĹ����в�Զ�����˴�ϳɻ飬�����ֳ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꣬���ž�ס���Ϲ⻯����ҡ������ձ��˺�ը�Ϻӿ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ߥ�ޣ�ֻ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˲���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ձ��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ѫһ�Ҷ��μ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�Ͷ�뵽�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ź�ĸ�ľ˾����ѫ����˰�������Σ���ĸס�У��˾�Ψһ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ϰ࣬ϱ���ڹ������ϰ࣬�˾����ѫ���ݺ������ڶ���ȥ���ͬ����ͬס���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ʧȥ����ϵ����ĸ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ѫ�����ֻص��˹⻯�أ�ֱ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Ⱥ������ĸ���ڹ⻯���سǸ�������ų���7��Żص��山ũ�塣�ҵ������ի�Ǹ����⾭����˫�ִ����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ֿ�����1945��8�¿�սʤ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ȣ��ִ������ź�ĸ��ԭ�����ص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ӻ���Ϊ����1947�����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;��Ѧ��ʱ��˳���Ѧ����Ѧ��կ����Ĺ��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ᣬ�������żҵ��ӻ����ֲ��ұ�կ����ڻ���У�һ�ѻ������˸����⡣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Ū�ˡ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⣬������ϼ�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½��ʱȴ���˸�����Ƭ�ߣ�����ص�ƶũ��
�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岻��, ��Ȳ��ֵij���Ĵ�С��, û������, ��ȴ�Ǹ�ʮ���ϵķ��ͽ, ������ʲô��֮ǰ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Ը, ���ڵõ�����ı��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ܷ⽨���Ӱ��̫����ڵ�������£�һ���Ӳ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û�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˻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ٷ��⣬һ����ṳ̂���رߣ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ˮ������զ�ֳ����ġ�û�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Զһ��Ͳ��ǵû�����·�����Գ����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Ŵ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ֵ����6����¥�ݵʰ�ÿ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үү���̹����磬û�˴���ÿһ��1���һ����̺��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żҼ�����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ѧ�ˣ��ű��ӻ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ڣ��ܴ���㣬��ź�һֱ�������ӵ����ܣ�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ܼҡ���1970����ʵ�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Ӹ���ɲ���˽����Զ�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ȥ���ܲ��ɣ���˽���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ˮ�����ض��˼��죬������˳��ȥ�⻯�ؼ����ɾ����ѫ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档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ž�ֻ��ĸ����һ��Ů����60���ͳ��˼���ġ��屣����1980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Ѫ˨�����Ӿͺ�Ϳ�ˡ�����û�а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ڵĶӸɲ�Э�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˽ӵ��Ҽ���ס������1984��˫˫�Ⱥ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ĵľ�������û��Ϊ����ֽ��Ǯ�������DZ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���Բ�ֻһ�ζ���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Ҫ�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ң����Ƿ�����ڣ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˸�������Ϸض���ֽǮ����˵: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֣������ſڵ����ӣ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̫���ᡣ��
���30���ȥ�ˣ�ÿ������ڵ�������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4�ֵ���һ���¾����Ϸ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ֽ��2006�������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뿪����12��֮�ʣ����Ǹ�4���ֳ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ִ��Ϊ����д�˸�С������ʯ�������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ķ羰��
�2014��8��28������ |